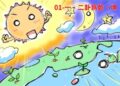廣和茶業原是武夷山老茶廠,目前保留山上最老的「品評室」 圖/陳維峰
陳維峰(台灣茶人、大學講師)
一、前言:為山而來,為茶而行
山行者,常為尋幽;茶人者,恒為覓香。此行武夷山,我並非初訪,但此次心念明確:為王廣和,為他所守的三坑兩澗九龍窠陳年大岩茶,為那福州岩茶發燒友口中的水仙老茶與金獎新作。王廣和者,廣和成掌門人,一位藏茶逾二十載、穿越四十年茶史風雲的岩茶藏家。其茶,其人,其道,一如古帖之真跡,表面平和,內藏風骨。
午後自武夷山北站入山,車行蜿蜒,遠山雲霧,山巒如畫,一路被峰色與茶氣溫柔接迎。抵達三姑石酒店稍事休息,入夜後即赴一場以武夷茶入饌的晚宴,茶香與菜香交融,既醒脾胃,也安人心。
飯後轉往茶廠,王廣和先生與夫人雖整日忙於接待,仍特意抽空親迎。白日裡他們方才接待完來自上海的藏茶老友,夜裡又與我們圍爐而坐。席間話語自然圍繞山場與茶事,談及岩茶之氣韻與老茶的性格,語氣不事雕飾,卻處處透著真情,彷彿談的不是茶葉,而是歷經歲月的同伴。
我們在一張金絲楠木大案前落座,茶具已備、水已沸。先品2024年慧苑坑金獎水仙,後啜1990年珍藏老水仙。一盞接一盞,舌底回甘,心中沉靜。這不只是一次品茗訪勝,更像是一場風骨與肌理、筆法與茶湯之間的深層對話。
二、金獎水仙與瘦金體:風雅骨氣的細筆線條
慧苑坑位於武夷山脈景區北面深谷,保留眾多原始林相。海拔適中、濕潤穩定、通風良好,形成絕佳的微型氣候。此地之土屬典型沙礫壤,排水佳、保溫強,生態豐富,常年不施農藥與除草劑。正因此,出產之水仙骨力內藏、香氣深幽,湯感潔淨,極少雜味。
廣和成的2024年慧苑坑金獎水仙,是一款在茶界頗具聲望的新作。其風格乃廣和成一貫之「無火之氣」——焙火後靜置退火,使火不張揚,而氣得其骨。這種處理方式對應書法中「藏鋒」筆法:火不現於湯面,卻藏於湯骨,讓香氣層次自然流轉。茶湯細緻清亮,花香顯,入口麥芽、果香輕盈,隨之而來的蜜香與淡淡米麥香,讓人不自覺又再嗅吸一番。
入盞沖泡,湯色明亮,茶湯一入口,便知其骨架結實,香氣細長。第一泡清亮,有桂花之氣,帶些枇杷的甜;第二泡花香更顯、麥芽甜湧現,湯中有一抹白蘭的清幽,且微帶雪梨般的果酸,使口腔明亮;第三泡開始展現層次的轉折,如筆法的「頓挫抑揚」,香中轉熟,喉間出現野蜜香的滑潤。至第七泡後,香氣並未退卻,反而多了一絲若有似無的骨韻,露出了山中歲月。
只道是火若可見,便非好火;香若即出,便難長留。其火攻中火而不烈,候以時間退火、呼吸,將煙氣悉數吐盡,留下的,是慧苑坑之原香,是如竹影掃階、松風入耳的輕音細語。
這一壺茶,無煙火氣,無脂粉味,卻有骨氣與文氣,令人聯想到宋徽宗《千字文》瘦金線條之美:瘦而不削,挺而不僵,筆筆見骨,字字透氣。正是一種骨勝於肉的高階表現,一種不言自威的沛然。

▲1957年,自然存放至今,博物館級別老岩茶 圖/陳維峰
三、老茶與米芾筆風:歲月沉潤的墨肉美學
相較金獎水仙的風姿綽約,1990年慧苑坑老水仙則屬「肉勝」之作。經過三十多年妥善陳藏,茶湯如筆墨積年,層層轉韻。首泡便有蔘香與果香交錯,之後熟果、胭脂、乳香次第湧現,氣息層層綿延,卻從不雜亂。那種轉折與遞進,正如米芾筆下飛白與側鋒並出,墨分五色之交錯節奏,淡中有濃,虛中帶實。
米芾書法以「肥而有筋,潤而帶骨」見長,不失鋒骨,卻富節奏張力。老水仙湯感厚實,卻不拖泥;香氣轉折,如筆勢跌宕;茶湯雖潤,卻有山場礦骨撐托,這種「歲月肉韻」,不屬軟腴,而是脈性豐滿、有節有制的書寫力量。
第二泡香氣變化顯著,從蔘香帶出花粉蜜香,宛如行草中的飛白筆勢,輕快卻不輕浮;第三泡至第五泡之間,香氣與湯感交互升沉,出現一種類似蔗糖與冰糖的複合氣味,餘韻深長,如秋水長天。
第六、七泡後,湯體開始轉為輕盈,卻仍具韻味,類似米芾書法後勢收筆之「勢斂而意展」。直到第十泡,口中依舊回甘,胸間溫熱不散,呈現出茶之真骨——時間所淬煉出的潤、藏、通、靜。
與其他市面常見老茶相比,這款老水仙毫無儲存霉氣,亦無火味上竄,顯見其倉儲得法。許多老茶偏濃偏重,而此茶則介於濃與雅之間,舉重若輕,宛若米芾一筆行草,既有潤澤之肌,亦不失筋骨之力。
此茶如《蜀素帖》,外放中有回收,奔逸之下有節制,毫無浮誇之感,反而給人一種熟悉而親切的時間肌理,如舊器皮殼般,有歲月的光澤與故事。
四、焙火如筆法:骨肉之間的氣脈調和
焙火,在岩茶中如同書法的墨法與用筆。過火如筆墨太濃,火味蓋骨;火弱如筆力不透紙,香氣無氣脈。廣和成之焙火精妙,金獎水仙為中火後退火,得香不見火;老茶雖不為自製,此嚴選之處盡見以火入骨,三十年後仍香潔不污。這種火之掌握,宛如書家提按之度、側鋒與中鋒之轉,既顯肌理,又藏骨勢。
2024金獎者,焙火勻而不滯,如瘦金體之細筆;1990老茶之火,厚而不焦,如米家書風之墨厚氣足。焙火不只是技術,更是一場關於氣息、節奏與陰陽調和的藝術操作——正如一筆書法背後的千鈞神思。
從徽宗《千字文》瘦金的風姿挺拔,到米芾《蜀素帖》的肉潤筆勢,廣和成兩款水仙各成體系,卻共享慧苑坑山場的精神氣息。金獎者如修篆之書,嚴謹精細,見工見骨;老茶則如即興行草,自由而不失章法。兩者並非對立,而是如書法中的骨肉相成——有骨者撐起格局,有肉者滋潤細節。
飲金獎水仙,神氣向上,喉頭涼甘如風穿竹林;飲老茶,氣沉入丹田,口腔溫潤如墨染宣紙。風骨與肌理,在這一杯一盞之中彼此呼應,既成對照,也成完整。
▲1990年醇厚舒服的老茶 圖/陳維峰
五、結語:茶為帖,山為紙,火為筆,歲月為墨
品廣和成慧苑坑水仙,不只是岩茶之精品,更是一場兩代風味美學淋漓盡致的表現。他們以茶為帖,以山為紙,以火為筆,以歲月為墨,領人如從徽宗瘦金之風骨,到米芾行草之韻肌的雙重書寫。骨肉之道,不止於茶與書,更在於對生命感知的層次提煉——從氣的貫通、香的節奏,到肉的厚潤與骨的端莊,最終抵達那一口「神遊未已」的沉靜甘甜。
回望此行,廣和成的茶,不是單為味覺設計的飲品,而是有書法精神、有山場文脈的文化作品。它們的風味,來自大岩茶的土與霧、風與礦,也來自焙火與靜藏的節奏掌握,更來自於藏茶家的品味對於時間、氣象與「骨肉兼備」的終極追求。
如今王董手中「年份高、品質佳」的高端老茶庫存已不足兩萬斤,多數早已被識貨藏家整批購藏。他清楚地知道:陳年不是價值,品質才是核心。真正經得起時間與市場考驗的老茶,從來都不多。我在離開前,再次向王董與夫人致意,感謝他們以茶為墨,寫下這兩款茶的風骨。若說書法是人的性情投影,那麼茶亦是山與人的心靈交界。廣和成慧苑坑水仙的「骨」與「肉」,正是這份交界處的最深回聲。此行武夷,於我,不只是品茶,更是讀帖,讀山,讀人心之骨肉——一場文字、火候與山靜水長的心適之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