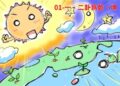福州茶會(作者拍攝)
文/陳維峰(台灣茶人、大學講師)
福州,毫無疑問,是中國武夷岩茶的超級戰區。
山那頭,武夷山雲霧繚繞,坑澗縱橫;而山這頭,福州悄悄收藏了大多數的好茶,如同深巷中的老屋,門扉不張揚,卻自有藏香之道。
朋友語帶驕傲地說,真正的好茶,大都留在福州,年輕人尤其敢買。只有極少數,會被送往北京,其餘城市僅得些許殘響。這裡,是茶的終點,也是記憶的集散地。這趟福州之行,自不可能冷場;茶席初展,便已是高潮。
有人笑說,這場茶會可說是「對台兩岸武夷茶文化交流」,誇張嗎?也許。但在這方靜室中,那幾款極少流通、難得一見的茶款如星光微現,令人心內悸動,竟也不覺浮誇。
茶會設於「雅道慢市集」的一隅。大桌如舟,沉穩地安放於深棕色布簾之下,一盞暖黃燈靜靜照亮茶席,是夏日午後的一束光,映在人與茶的呼吸之間。今日主泡者是一位氣質內斂、手法沉穩的90後文人妹妹。壺泡與蓋碗之間,她的節奏如松林間風,不疾不徐,自帶安定之氣。
千里關山,以茶會友,席間幾位愛茶人無不識山場、懂焙火,其中最讓人敬重的大哥,據說早年曾任武夷山高階相關職務,如今已退休,往返於茶山與茶席之間,低調而安靜,是一種歲月沈澱後的自在。
一開場便是福州朋友自己的訂製款——正岩秘境山場的名叢。品飲時,舌面上的澀感,迅速化開為甘,轉化的潤澀,這是正岩茶的質地表現。除了澀感以外,嘴巴裡還有收斂性,這是極為關鍵的感受,它不同於前述舌面上的澀感,而是更深層、更立體的感知。當我們啜飲一口高質量的武夷岩茶,那種微妙的緊縮感並非出現在舌尖或舌面,而是出現在口腔的兩側——也就是臉頰內壁的位置,那裡像是被「捉緊」了,這正是收斂性的體現。

▲各色茶品(作者拍攝)
這種收斂性不刺喉、不苦澀,反而是結構感的展現,是「岩骨」之所在。當這種緊實的收束慢慢緩解,轉化為細緻綿長的甘甜時,我們可以感受到茶質的層次與深度。那不是瞬間的香甜,而是一種由內而外、從緊到鬆、由澀轉甘的過程——帶出悠長的回甘與氣韻流動。這種從「捉緊」到「釋放」的品飲過程,是高端武夷岩茶獨有的魅力,也是我們是否能真正理解大岩茶的試金石。
再一次,那樣的澀感、收斂性在第二款茶裏炸開了!取名為「岩骨花香」的天心岩肉桂「16888」,真如其名,來自於天心正岩茶業有限公司,天心正岩茶葉科學研究所監製。老茶廠的原料果真是硬底子,超乎大家預期的香氣、滋味和湯感,相較於第一款,茶香氣明亮奔放,湯感剛猛乾淨。2022年的茶,價格也是武夷山到頂的,單泡10克人民幣1200元,合計一斤6萬,恰好在官方許可的範圍。令人佩服的是,分享者和前款都是同一人,90後的茶人妹妹,福州喝岩茶的年輕一輩真不簡單!
就在眾人驚嘆之際,真正的壓軸悄然登場——老領導的私房茶。老領導說話極其謙遜,卻偶爾流露出當年走南闖北的風彩。他聊起過往與台灣的來往經歷,從北到南,政商兩界皆有足跡與交誼。談到早年武夷山這些茶企的草創歲月,他語帶感慨:「那時除了茶之外,大家一起幹,一切從零開始。」
第一款茶湯初入口,很舒服的感覺,像是冬天融雪之後的第一道陽光,暖洋洋地流入丹田。細膩的花粉、花香在喉頭開展開來,隨之而來的是極穩定的茶氣推進,也如同一股微潤卻堅實的山泉,自舌根一路穿入腦後,留香不散。茶湯中礦物氣息與草本甜感並存,早已無焙火的銳利,也不見流行口味的討喜張揚,反而展現出一種「不迎合」的溫和堅定,這是一款稀有名叢,山場在慧苑坑深處的古井,古井的茶從不讓人失望。
四款茶最後壓軸的是十八寨肉桂。
十八寨山場位於九龍窠的正上方,是母樹大紅袍所依岩體的崖頂地帶。從地質與氣候條件來看,它擁有難得的崖頂微氣候:通風良好、日照集中於午後短時段,濕度恰到好處;同時與母樹大紅袍共享相同的岩脈土質,卻因地勢更高、地形更窄而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香氣結構。這裡不是典型的窠、澗、坑,而是夾於兩峰之間的狹長石磴,原為武夷山寨型居住地,今多為無人山林。
民國初年,蔣希召曾於《遊武夷記》中描述:「入九龍窠,窠為天心永樂寺,植茶最繁之區,極品之大紅袍即產於是,谷極狹長,約三里,谷底一岩突起,高可三十餘丈,曰龍頭岩。岩半有水滲出,所謂大紅袍名茶即植於岩下。」此「谷底之岩」的頂部,便是今日所知的十八寨。
據傳,此地曾有十八株名叢母樹齊聚,包括如今極稀少的不見天、大紅梅等。現今僅存一株大紅梅仍由曦瓜香江三兄弟照看,成為這片山場僅存的歷史見證。
兩款壓軸茶的包裝其實是「圖文不符」,要嘛無註記,要嘛無關乎上頭落的茶名,然而確實如上商標一樣,乃是出自於曦瓜。
曦瓜香江茶業於十八寨握有的茶地,其中一段為1990年代初種下的肉桂,維持「留欉放養」的栽培方式。這代表茶樹多年不修剪、不催芽,任其與岩土風氣共生。這樣的管理方式既費工又高風險,卻換得一種真正靠時間積累的香氣密度與氣骨結構。
這一小批十八寨肉桂,乃由曦瓜三兄弟當中的徐秋生師傅親手製作,不外售,也從不上架。據說茶廠內的手工搖青區,會特別為此茶預留製作時間與空間,連焙火程序也與常規商品茶完全分離,確保其香氣不受任何干擾。
我在這場茶會裡,啜茶如思。那一刻,周圍人的聲音與茶室的背景都淡了下來,只剩那一口茶湯的通透與醇厚,如同一段從未命名的旋律,緩緩進入內心深處。這不是品評,這是遇見。
在喝到十八寨肉桂之前,極少想過「香」與「骨」這兩個字,可以在一泡茶湯中這樣彼此成全。

▲肉桂(作者拍攝)
茶湯剛入口,還未咽下,已然感受到一股極輕卻立體的香氣在口腔中展開。這不是一般肉桂茶常見的辛香或濃焙香,也不單是單一的桂皮氣息,而是一種帶著陽光溫度的花粉香與奶香交融的氣息,像午後走進一片曬過的野地,腳步驚動了草叢,粉塵與青草氣隨之飄起。
它的香氣帶有十八寨特有的開闊感與乾爽度,不潮,不悶,也不帶山谷濕氣。與慧苑那種青苔、朽木氣不同,十八寨的氣味更「亮」,更貼近山坡午後的日照與風,香氣是乾淨的,帶著潔淨石頭表面曬乾後的礦物氣,卻不刺鼻,反而溫柔地攤開在舌面與鼻腔之間。
而那香氣不是浮在湯面之上,而是與水體緊緊交融。茶湯的結構極其平衡,沒有任何厚重或滯留,卻極富存在感。入口時溫潤如絲,沿舌中滑過,兩頰隨之開展,喉頭被一層極淡的涼意輕輕帶過,像是風穿過石縫,來得乾脆又不突兀。
第二、三泡時,茶湯的味道開始轉化,初始的奶香與花粉感漸漸讓位給草本與果香。那種香像是薄荷梗與野薑花融合,夾雜著極細緻的桂花與蜜香,並非果乾型的甜,而是一種淡入舌根、逐漸泛出來的柔和甜韻,如柿皮、清甜梨肉或成熟無花果的皮層。
水體之下,則是一股極為穩定的「骨感」。這種骨感並不沈重,而是一種支撐茶湯結構的力量,像茶氣之骨,從口腔延伸至咽喉、再往下胸口推進,留下安定與回甘。那甘不是鋪天蓋地的生津,而是一種喉底慢慢開展的甜,如岩縫中流出的水,滴而不止,清而不喧。
直到第五泡之後,香氣逐漸內斂,湯感依然堅實,仍然維持著通透不濁的骨架。此時再回望第一泡,才真正明白這款茶的節奏不是鋪排式,而是「逐層卸下、逐步深入」。它沒有第一時間衝擊你的強烈感受,但每一泡都在向你靠近,每一層都在訴說它的身世與性格。
十八寨肉桂是一款「不趨附」的茶。它不屬於那些標榜濃香、厚焙或年份的類型,也不依賴話術與包裝來說服你。它只以茶湯自身的通透與安靜,講述著崖上陽光、礦石、老樹與製茶師傅手勢的痕跡。它所留下的,不是香水般的氣息記憶,而是一種山風與茶火的氣骨。
這樣的茶,不是為眾人準備的,而是只為那些願意靜靜喝完六、七泡之後,才開始真正感受到它存在的人而來。喝它,需要一點時間,也需要一點對香與骨的理解。而當你喝懂它的那一刻,你會知道:這香,不是為鼻子而設;這甘,不是為舌頭而生;而是為整個人,身心安靜時的深呼吸。
茶會結束後,我帶著茶香與午後的夜氣走出雅道集。回首這一桌,不可不謂是真實地超越了前些天在武夷山的茶,我明白了一件事: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茶,屬於非賣品,不見聞於茶榜,有錢也買不到,只留在老闆的口袋裡,還有極少數他非常必要、特殊的關係上。這天我有幸遇見了,它在口腔中留下的,不是香,而是一種被岩與風洗過的安靜感。
這幾泡茶,不是天花板,而是天花板之上的那一層,絕少被外界打開過的天窗。愉悅的,亦或幸福感,莫不心滿意足,心底依舊澎拜不已,但是這樣的好,以後也再難出現,喝過就該忘了它吧⋯⋯